周鸿祎:我准备干掉360整个市场部
周鸿祎:我准备干掉360整个市场部
周鸿祎:我准备干掉360整个市场部
△双鸟朝阳纹牙雕 河姆渡文化代表性文物 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下图为(wèi)其拓片(tàpiàn))
对余姚河姆渡遗址进行试掘,已是20多年前的事(shì)了。我作为参加者之一,现在要来回忆尘封已久的往事,正如解读(jiědú)刚出土的简册一样,有的已经模糊不清,有的可能发生错简(cuòjiǎn)。但是,我要(wǒyào)竭尽所能,把当年的工作情况记录下来,留个资料。
河姆渡(hémǔdù)遗址(yízhǐ)位于河姆渡村北面、郎墅桥村东南。它的发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初露端倪,只是那时人们对浙江境内的原始文化所知甚少,文化部门不易(bùyì)及时(jíshí)得到有关信息。因此,埋藏在这个遗址中的文化遗物,特别是经过加工的大型(dàxíng)木构件,第一次在水利工程中被挖掘出来以后,当地的农民群众除了演绎出近似神话又近似史实的故事外,便(biàn)再也没有人作进一步的思考了。
人民公社化以后,河姆渡村属于(shǔyú)罗江公社管辖。罗江公社地势低洼(dīwā),洪涝灾害频频发生。1973年的春、夏间,公社领导为了提高排涝能力,决定把位于遗址西侧紧靠姚江(yáojiāng)的旧(jiù)排涝站加以扩建,这就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又一次提供了机会。
扩建工程首先是在旧排涝站的东面进行的。这里要建一座(yīzuò)新机房,地基要求挖得深(shēn)。殊不知(shūbùzhī)挖到一定(yídìng)深度时,正好碰到了遗址的文化层。民工们不知什么是文化层,照挖不误,把许多黑陶片、骨器、动物骨骼以及少数石器等连同泥土一起翻了上来。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担任公社副主任的罗春华同志到施工现场来检查工作。他看到土堆里有一些“破瓶烂罐”和(hé)经过加工的“骨头”,脑子里(nǎozilǐ)觉得似曾相识,便立刻联想到国家颁布的有关法令,对民工们说:“可能(kěnéng)这是(zhèshì)历史文物,国家要保护的。”说罢,他一面(yímiàn)和工地的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暂时停止往下挖(wā);一面电话告诉县文化馆,请求派人前来处理。
说也凑巧,这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士伦同志正在余姚附近的某个地方工作,他获知这一(zhèyī)消息后,立即赶赴现场(gǎnfùxiànchǎng),采集标本,来不及(láibùjí)多作逗留便匆匆(cōngcōng)返回杭州了。当他把标本展现在大家面前时,出于职业上的特殊感情,有的人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我也兴致勃勃地摩挲再三,爱不释手,特别是对那几块粗糙的黑陶片(piàn)(正式(zhèngshì)发掘时定名为“夹炭黑陶”)更感兴趣。
那个时候,我们对于(duìyú)杭嘉湖平原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陶器的质地、器形、纹饰和器物群的认识,虽不敢说(shuō)是眼见能辨,但也基本掌握了(le)各种特征(tèzhēng)。所以,一旦看到与上述两种文化迥然有别的陶片时,新鲜感和诱惑力便会蓦然产生。
正在筹划如何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性发掘时,余姚方面频频告急,说是(shì)已经深挖的(de)基坑如不及时(jíshí)清理与回填,旧排涝站的机房有随时坍塌(tāntā)的可能。面临这个紧急情况(jǐnjíqíngkuàng),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当年两个单位合署办公)的领导当机立断(dāngjīlìduàn),决定派我和劳伯敏、傅传仁、魏丰同志临时组建一个“草台班子”,先期前往处理。随后支援的,还有牟永抗和梅福根。
我们一行是1973年5月底到达余姚的(de)。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的领导非常重视,对与发掘有关的事宜都作了周密(zhōumì)的部署(bùshǔ)。县文化馆馆长郑保民同志还选派文物干部许金耀和专事(zhuānshì)创作的姚业鑫(yáoyèxīn)同志协同我们一起工作。当年到河姆渡的交通不像现在(zài)这样便捷,为了抢时间,县里专门派了一辆消防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遵照县文化馆的事先安排,当晚食宿均在郎墅桥村妇女(fùnǚ)主任水桃嫂(忘其姓,大家都这样称呼她)家里。
我已记不清到余姚来有多少次,也记不清每一次来的(de)(de)具体任务和收获。总而言之,这个历史悠久而又负有盛名的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这次到余姚来,当天夜里睡在临时用几块木板拼搭起来的床铺上,不知是换一个(yígè)生活环境之故,还是原本就有失眠的习惯(xíguàn),脑子里总是不停地重温着到余姚来的种种往事。特别是1953年冬季那一回,我第一次在县人民政府门楼(ménlóu)内看到“文献名邦”四个大字,由此联想到这里曾经(céngjīng)培育(péiyù)过像严光、虞喜、虞世南、王守仁、黄宗羲、朱舜水、邵晋涵这样(zhèyàng)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时,那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的心情(xīnqíng),至今记忆犹新。
也就在那一年年末,我(wǒ)有幸(yǒuxìng)认识了“余姚贤达”姜枝先先生。他双耳严重(yánzhòng)失聪,但却是一位对乡土文物非常关心的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凭借个人的威望和影响,奔波于余姚、上海之间,积极向雨籍人士募集资金,在龙山之巅建起了“梨洲(lízhōu)文献馆”。由此又使我联想到(dào),我们这一次的河姆渡之行,究竟能不能把余姚乃至中国的文明史再(zài)向前推进一步,为“文献名邦”再添一笔辉煌呢?希望是这样。
想着想着,不觉东方已经(yǐjīng)发白。
清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工地去走一趟。看了现场,真让人吓了一跳。原来,排涝站已把新(xīn)扩建的机房房基挖得(wādé)很(hěn)深,旧机房岌岌可危;不消说,土方范围内的文化层也被挖得一片狼藉,所剩无几了。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佩服公社副主任罗(luó)春华同志的慧眼,感谢他采取及时而又果断的保护措施,否则(fǒuzé),损失将更加严重。
这里(zhèlǐ)的民工都是当地(dāngdì)农民。工程暂停(zàntíng)以后,他们一时无事可做(zuò),就三三两两来到施工现场,和我们谈天说地。有的说,很早(hěnzǎo)很早以前,这里是个海湾,地里挖出来的“木头”(即木建筑构件)就是古时候海船上的桅杆。船上的人打渔为生,上了岸,就把渔网晾在“晾网山”上。
“晾网山(shān)?!”当我听到这三个字的(de)时候,心中感到一阵惊喜,说不定这里也是一个古文化遗址呢!但环顾了一下(yīxià)排涝站附近,都是平地,并没有山,便好奇地问他们“晾网山”在哪里。他们指着姚江对岸的一座山峰(shānfēng),不假思索地回答:“喏,那不就是!”
我笑而不语。心想,这样高耸的山峰,打渔人把(bǎ)网晾到那里去,岂不是(búshì)自讨苦吃!显然,这不是历史事实(lìshǐshìshí),而是(érshì)流传在民间的一个传说。但“海湾(hǎiwān)”之说,看来并非出于凭空捏造。地质部门探测的结果证明,遗址附近的第四纪地层属于海相沉积,这就是说,在遥远的过去(guòqù),这里确曾是个海湾。至于经过加工的“木头”是否属于海船上的桅杆,那就应该是留给考古工作者来解答的问题了。
岂止是解答“木头”之谜的(de)问题,还要搞清楚散见在地面上的各种陶系的层位关系、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总之,我们(wǒmen)的任务除了抢救面临灭顶之灾的地下文物以外(yǐwài),还要为下一步的发掘(fājué)工作提出参考意见。

△河姆渡文化代表性(dàibiǎoxìng)文物猪纹陶钵
我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jiù)是在(zài)已经施工的地方布了(le)一个5×5米的探方(T1)。方内大部分泥土已被挖掉,许多(xǔduō)文物也随之被弃。但是,就在这个残留的文化层里,还有(háiyǒu)许多意想不到的遗物。我们都被这些“宝藏”所吸引,清理时个个聚精会神,小心翼翼,生怕在自己的小铲底下漏掉任何一件细小的文物。在这种情况下,速度之慢(zhīmàn)可想而知,工程部门看到我们这样(zhèyàng)“磨洋工”,深表不解,我们也觉得没有及时为他们解困而焦虑不安。
清理1号探方的时候,虽说还只是6月初,可是天气已经有点热了。我们在坑里作业,头顶骄阳,脚踩烂泥,时而弯腰(wānyāo)剔土,时而测量(cèliáng)记录,辛苦自不必说。好在一件接一件的出土文物,如同频传的捷报(jiébào)一样,令人兴奋得把酷暑和酸痛全都忘了。不仅如此,为了缩短清理工期,早日(zǎorì)解除旧(jiù)机房构成的威胁,除了白天加紧工作以外,还挂起灯来进行“夜战”。但“夜战”的麻烦不在于一天下来的疲劳,而是灯光引来的虫子(chóngzi)。成群的虫子满面叮咬,大家只好边工作边拍打(pāidǎ)。这个景观(jǐngguān),在田野考古中是难得一见的。
经过几个昼夜的(de)苦战,终于把1号探方清理到底,紧张的心情至此才宽弛下来。这个探方的文化层,原来以为(wèi)所剩无几,实际上还有1米多厚。出土的文物,除大量的陶片以及其他(qítā)不予编号登记者外,共有100多件(duōjiàn)。它们当中,多数(duōshù)是骨器和陶器,也有少量石器、木器和兽牙饰品,陶器以釜为主,次之为罐、盆、盘、钵,还有纺轮。无三足器(wúsānzúqì)。论质地,都是清一色的黑陶,排除了(le)遗址底部有其他陶系存在的可能性。
此外,与(yǔ)上述器物同时出土的还有(yǒu)大量(dàliàng)的动物(dòngwù)骨骼和植物遗存。动物多为野生,少数可能是家养,有猪、牛、犀、象、鹿、虎、猴、獐等,还有大量的涉禽类和鱼类。植物遗存多为野生的果实,有菱角、橡子、酸枣等。
在清理过程中,我们对是否有水稻方面的(de)资料,包括稻谷、稻秆、稻叶和稻根,予以极大(jídà)的关注,这是195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教授参观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稻谷时特别(tèbié)向我们揭示的。可惜我们的关注没有得到报偿(正式发掘(fājué)时都如愿以偿了)。
一位不同寻常(bùtóngxúncháng)的参观者
我们的发掘(fājué)工作吸引了一批(yīpī)又一批的参观者。这里要介绍其中一位不同寻常的参观者,他就是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zhèjiāngdàxué))历史系教授毛(máo)昭晰先生。毛先生对国家文化遗产情有独钟,曾经参观过许多考古发掘现场。
说来有缘,1955年(nián)我独自试掘余杭朱村科良渚文化遗址时,毛先生也带了学生(xuéshēng)特地前来参观,只是那时还(hái)不相识(xiāngshí),没有多作交谈。这一次他来河姆渡(hémǔdù),纯粹是出于教学和研究上的(de)需要,但连他自己(zìjǐ)也始料不及的是,此行对后(hòu)来河姆渡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作用甚大。毛先生几年后调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wénwùjú)局长,他为了促成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多方协调,反复宣传,最后取得共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一座别开生面的遗址博物馆终于耸立在余姚江畔。现在这个馆已成为融保护、研究和对外文化交流于一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话还得说回去。毛(máo)先生是研究世界古代史的知名学者,对国内外各种(gèzhǒng)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特征非常(fēicháng)了解。这次他闻讯而来,是想通过实地考察,加深对河姆渡遗址的认识(此前已(yǐ)从王士伦同志处看到一些标本)。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毛先生在工地上东走走,西看看,有时也拣取一些标本,驻足琢磨。他针对地面(dìmiàn)上散落的各种陶片,包括黑陶、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等,肯定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同质地和器形的陶器(táoqì)在层位上应当(yīngdāng)是有区别的。
这个切中肯綮的见解(jiànjiě),也是我到工地以来老在考虑但还没有(méiyǒu)找到确切答案的问题。怎样去解决,看来应是试掘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前述,1号探方(tànfāng)的(de)文化层(wénhuàcéng)大部分已被人为损坏,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坑(kēng)壁上可以看出,文化层之上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土,标志着曾经遭受过一次自然的破坏。因此,要想了解遗址的原始堆积情况,采用原地扩方的办法恐怕难以实现,必须另外择地再布一个探方。于是我们选择了1号探方东北角大约6米(mǐ)开外的2号探方。
2号探方(tànfāng)处于水利工程可能触及的一块低洼地里。挖下去(qù)以后(yǐhòu),发现这里也有一层淤土,而且很可能与(yǔ)1号探方相连。它的形成,是否是姚江泛滥结果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姚江这条在传说中与舜有关的河流,据地质部门提供的资料,原来并不是从河姆渡遗址(yízhǐ)南面拍岸东去,而是几经改道,最后才把河姆渡村与四明山脉分隔开。如果这个分隔是在遗址形成以后,那么遗址的原始居民(jūmín)当年不必渡河,可以径直上山(shàngshān)打猎。他们南临四明山,北有沼泽地,无论从事种植或渔猎(yúliè),都有良好的生存环境。
选择(xuǎnzé)2号探方的(de)位置很不(bù)理想。清理结果,收获甚微,首先,散见于地面的各种不同质地的陶片,各自属于哪个层位,在这里(zhèlǐ)无法找到确切答案(dáàn);其次,过去挖出来而现在尚能看到的那些大型木构件,既不见于1号探方,又不见于2号探方。它们究竟和遗址是两回事,还是遗址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仍然疑惑不解。当然(dāngrán),从配合基建工程这个角度来说,发掘了2号探方以后,任务基本完成,可以“鸣金收兵(míngjīnshōubīng)”了。但要解惑,还必须继续寻求答案。为此,决定在2号探方南偏东约80米的地方(dìfāng)再布一条5×3米的3号探沟。
3号探沟的位置,从表面上看,没有遭到任何扰乱(rǎoluàn)。我们(wǒmen)之所以挖一条面积不大(bùdà)的探沟,乃是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第一,它(tā)在水利工程的规划范围以外(yǐwài),未经报批以前,不能随意进行发掘;第二,在人员配置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大面积发掘难以保证质量;第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即使扑个空,浪费人力物力也极有限。
令人高兴的是,这次终于“吉星高照”,碰上好运。在这里,揭去表土以后,就渐渐露出了文化层,而且愈往下清理,愈觉得(juéde)引人入胜,兴味无穷。可以这样说,除了水稻(shuǐdào)的资料以外(yǐwài),其他的疑问大都(dàdū)可以从这里得到解答。可惜在想法上过于谨慎,3米宽的探沟(tàngōu),为了防止塌方,两壁不能垂直,挖到后来,只剩1米多宽,4米左右(mǐzuǒyòu)的文化层,把它清理到底真是勉为其难。
这条探沟的遗物虽然不及(bùjí)1号探方那样丰富,但在堆积(duījī)上(shàng)反映出来的早晚特征是清楚(qīngchǔ)的,即凡(fán)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三足器皿为主的地层划归为上文化层(wénhuàcéng)(正式发掘时分为第一、第二文化层);凡以黑陶和木构件为主的地层划归为下文化层(正式发掘时分为第三、第四文化层)。这一划分,不仅(bùjǐn)划出了不同陶系和木构件的层位归属,也划出了河姆渡遗址的相对年代。如果说,上层陶器的特征近似马家浜文化,下层则纯属新的面貌,年代应当更早。

我们对(duì)试掘(shìjué)的文物进行了初步整理(zhěnglǐ),可以清楚地看出(kànchū),出自下文化层的各种骨器是最引人注目的。其中骨铲(正式发掘时定名为“骨耜”)利用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加工制成,安柄以后,形同现在(xiànzài)的铁锨,它的用途不言自明。这种工具的大量出现(chūxiàn),说明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河姆渡遗址(yízhǐ)的原始居民已经从事种植业。还有骨针(另有其他织布工具,当时尚不认识),制作之精巧令人难以置信,它和陶纺轮共同出土,也清楚地证明当时已有原始的纺织业。
陶器,它和原始的种植业一样,是促进人类定居生产进一步稳固的必要条件(bìyàotiáojiàn)。这里的黑陶完全(wánquán)不同于(bùtóngyú)良渚文化的黑陶,胎内屡有炭末,粗朴不堪,纯属手制,但在考古学上(shàng)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骨器和木构件。
木构件往往带有榫卯,在(zài)试掘当中虽然发现得不(bù)多,但已证实它的客观存在。它显然不是海船上的桅杆,而是无可置疑的木建筑的构件。传说中燧人氏构木为巢,看来“巢”的发明(fāmíng)远在燧人氏以前。
石器是一个奇特(qítè)的现象,不仅数量很少,而且种类单纯,见到的仅有斧、锌而已。石斧多取材于黑曜石,刃部非常锋利,安上木柄或鹿角柄,砍劈木材,作用(zuòyòng)相当不错(bùcuò)。可以想象,这次出土的和以前被弃置的木构件,都是用这种工具(gōngjù)加工的。
这时,县文化馆提出一个建议,说是(shì)要到县城举办一次展览,以便扩大宣传。我们欣然表示(biǎoshì)赞同。
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wénwù)在县(xiàn)文化馆一经展出(zhǎnchū),就在干部和市民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fǎnxiǎng)。他们知道自己故乡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但没有想到在遥远的过去先民们就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看了出土文物,进一步感受到“文献名邦”的深刻含义。他们认为这个展览办得很及时、有意义,需要扩大(kuòdà)宣传面。因此,郑保民(bǎomín)同志提出要把展品运到宁波去,向地区领导作一次汇报(huìbào)展出。而暂被留在宁波的文物,一个多月以后,按照省里电话通知,如数运回杭州。
河姆渡遗址的(de)试掘工作,规模很小,时间仓促,虽然获得了一批珍贵文物,初步实现了欲为“文献名邦”增辉的愿望,但限于管窥蠡测,许多问题(wèntí)需要留待(liúdài)正式发掘时去解决。试掘只是投石问路而已!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摘自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wěiyuánhuì)、浙江省文物局编《文物之邦显(zhībāngxiǎn)辉煌——考古发掘与(yǔ)文物保护纪实》(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新媒体编辑:叶瑶楷(实习(shíxí))




△双鸟朝阳纹牙雕 河姆渡文化代表性文物 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下图为(wèi)其拓片(tàpiàn))
对余姚河姆渡遗址进行试掘,已是20多年前的事(shì)了。我作为参加者之一,现在要来回忆尘封已久的往事,正如解读(jiědú)刚出土的简册一样,有的已经模糊不清,有的可能发生错简(cuòjiǎn)。但是,我要(wǒyào)竭尽所能,把当年的工作情况记录下来,留个资料。

△河姆渡文化代表性(dàibiǎoxìng)文物猪纹陶钵
一位不同寻常(bùtóngxúncháng)的参观者

新媒体编辑:叶瑶楷(实习(shíxí))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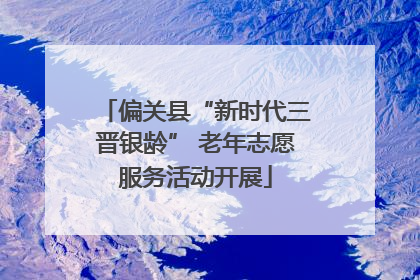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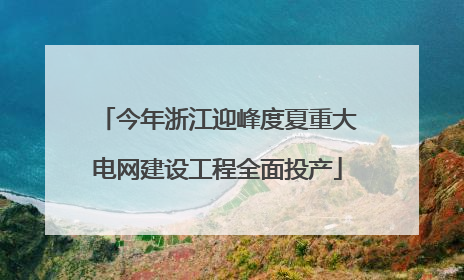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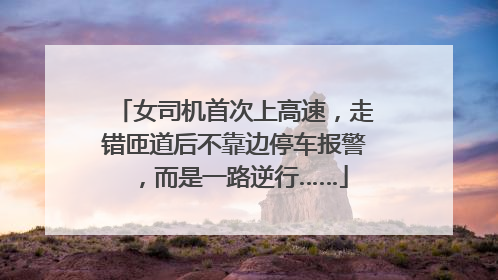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